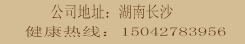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繁衍 > 郑晓红当一树红蓼低于黄土高于塬畔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繁衍 > 郑晓红当一树红蓼低于黄土高于塬畔

![]()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繁衍 > 郑晓红当一树红蓼低于黄土高于塬畔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繁衍 > 郑晓红当一树红蓼低于黄土高于塬畔
当一树红蓼低于黄土高于塬畔
郑晓红
1.我以为那是一棵正开花的树。可祖母说,那只是一棵没名堂的草花。我站在我以为的花树下面,头一歪,脑袋抵在祖母腰窝那里。祖母也站在她说的草花下面,一手揽住我的肩,一手揪下一穗花,花树抖几抖,又平静下来,挑在梢头的花穗超出她头顶许多。祖母的院子里种的都是有用的植物。我那时总觉着,许是经了人手侍弄的缘故,对人有用的植物都长得丑。茄子丑,青青紫紫,被太阳晒出好些疤,一些疤收缩地凹进去,一些又暴突出来。毛剌剌青嫩的俊黄瓜要拌凉菜,吊在蔓上留着做种的黄瓜蠢笨极了,龟裂成干河床样的表皮捂着个饱胀的大肚子。辣椒更难看,皱巴巴的,曲里拐弯的,还有好些辣胆包天的虫子早早把卵产在辣椒芯里。豆角的丑我能忍,实在因为不起眼的豆荚里面天知道藏着什么颜色什么花纹的豆子,剥豆子就像猜谜,像探险,像撞大运。芫荽还算好看,细细碎碎的,像山里密林下面的蕨类植物,可是,我那时怕吃芫荽,像读不爱看的书要跳行一样,它就是要紧赶几步跳过去的那几行。没用的植物都俊。一打春,紫花地丁一夜之间冒出来,过几天,细碎繁密的地胡椒花铺开来,各种醡浆草的黄花晶亮晶亮,婆婆纳的小蓝花星星点点,碎米芥散发着淡淡的辛辣味……这些小草都不起眼的很,小花朵细碎的非得趴在地上才看得清。还有最叫大人们不待见的各种蒿子草,白蒿幼时叫茵陈,像铺开在地上的灰绒花,青蒿很臭,开完不起眼的花之后结出一粒粒骄傲的小种实,叫我看不够。可惜,那些小草花常常被碾歪在大人的脚下,或者,不等开旺就被牲口的舌头卷了去。我以为的花树也无用,它不是祖母种的,不是叔母叔父们种的,不是堂姐们种的。没人知道打谁家飘来那么一颗种子,落在墙根下,因为不碍蔬菜的事,也不碍院里人的脚,就顺顺当当长大了。其实它旁边原本还生有灰条条草,青蒿白蒿,狗尾巴草……但院子里有个把小脚当鼓槌使唤的祖母,凌晨鸡一打鸣,就踩了紧密的鼓点院里院外咚咚响,鼓槌擂到墙根下,那些熟稔的野草就没了活下去的余地。唯有这一棵,许是天生就比旁的物种结实些,一贯心明眼亮的祖母误判了它,拔草的手一跳,越过去,留下了无用的它。我撵着祖母问它的名字,祖母说,去去去,到外头耍去。大人对自己不知道的问题向来没有好声气,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仿佛小孩子打搅了他们正在做的大事。我拌在忙活着干大事的大人脚底下,问遍了院子里所有人。祖母在厨屋里踩着板凳俯在案板上揉足够十几口人吃的大面团,面团翻过来倒过去地揉,揉成云朵,揉成草垛,揉成棒槌,揉面的间隙,灶火里的风箱拉的乒乓响。叔父叔母们在掰玉米,砍玉米杆,翻地,玉米棒子一对一对结在一起,一些搭在横杆上,搭成矮敦敦的黄金桥,一些一圈圈向高处搭,像要在院子里树起一座金色的灯塔,还有些搭在已经卸了果的果树上,院里的树全被打扮成玉米树。在我看来,他们就像在做游戏,做得忙忙碌碌,汗流浃背,顾不上理人。祖母磨不过我,甩过来一个名字。叫洋荞麦。——洋荞麦跟小麦一样都是粮食吗?——为什么叫洋荞麦,还有土荞麦吗?土荞麦长啥样?——小麦为什么不像它一样开出一穗子一穗子的花絮絮?——它开完花是不是要结麦穗了?——为啥不像种小麦一样种一大片洋荞麦田?祖母恼了,冲着院子里喊,快拿镰刀来把墙角角那祸害砍了去。我闭了嘴,跑到院子里,站在花树下面对着它喊,不问了不问了,再也不问了。可是,它怎么会是一株草呢?有比两个我摞起来还高的草吗?有枝叶开张出一蓬树冠的草吗?有分枝像主干一样结实一样长出花穗的草吗?它虽然长在墙根底,但它的枝干舒展的那么自由,因为孤独而自由,就像光光的山峁上独独一棵树,就像平展展的地头上独独一棵树,就像天边落日的剪影中独独一棵树,就像石峡延伸到尽头合了缝挤出的独独一棵树,就像悬崖上眺望着的独独一棵树……它明明就是一棵树啊。或者,一株草也能活成一棵树的样子?2.离开祖母的老屋,回到我的出生地,一个叫烟景川的被群山包围的油田小农场。在同龄的伙伴中,我是一个笨拙的孩子。打沙包,我是最先被打中的那个。跳房子跳皮筋跳绳,我是最先歇场的那个。抓子的时候,别人将子儿抛高高的,手底下啪啪啪跳几下,又轻悄又灵巧,轮到我,要么手碰了其他的子儿,要么接不住空里落下来的子儿。玩“张飞追燕子逃”的游戏,追时总追不上,逃时却最先被逮住。所以,每当伙伴们分组对阵,我就成了双方都不肯要的那个。他们呼啦啦玩将起来,我一个被抛下。还好,群山之间,到处是无人搅扰的野地。千万只昆虫纵情鸣唱,仿佛明白自己是山野的主人。它们不拿我当外人,毫不防备,把每棵树,每株花,每块石头当成恣肆的舞台。大多数蛐蛐直着嗓子“吱儿——吱儿——”叫,它们对当下的生活感到满意,不认为要使用多么费力的技巧来炫耀自己的歌声,觉得需要唱几声,张口就唱了,闲散地唱,没心没肺地唱。偶然有蛐蛐会发出“唧唧吱——唧唧吱”的异样的鸣声,似乎竭力按捺狂喜,声调里有讨好的挑逗。我便知道,前方那棵生着红果的小灌木下面,有雄蛐蛐邂逅了意中人,正骄傲地站在一株草下,激烈地振翅,竭尽所能奏出最美妙的乐曲。野地那边,乱草掩盖的一堆乱石下面,骤然传来带了颤音的“吱……”声,像激情来临前压抑的颤抖,又像激情后蓦然哑了嗓子。哦,一对蛐蛐结婚啦,它们正藏在石头下面,进行天籁掩护下的交配。它们如此忘我,因为活着放声歌唱,因为爱情放声歌唱,因为繁衍放声歌唱,也许,它们在秋凉后告别世间的最后一刻,也会尽力发出“吱……”的奏鸣。被同类抛弃的孩童,在异类的领地里找到了自在与自由。她巡视一面又一面野山坡,草木簇拥,虫鸟齐鸣,她一声不响,威严的像王。她巡完脚力与胆力能及的野地,都没有看见祖母老屋院子里的那种花树一样的大草。山坡上数点惊心的红随风跳荡,那是山丹丹。山丹一开,几支花瓣都拼力向下翻卷,全身绷紧,仿佛总嫌舒张的不够。它这样怒放,红的自然更夺目,开的是一朵朵火焰,想将山坡燃尽。所以,山丹的植株虽矮小,气势却逼人,每朵花都震得我屏息,心脏嗵嗵跳。我害怕这种叫人不平静的花儿,宁肯坐在不远处一株长满刺的飞廉旁边,远远地瞧着它。河岸边成片的是香蒲,密蓬蓬的长叶子从水里伸出,举起一根根水烛。父母每年都采些蒲棒回来,把蒲绒褪下来填实枕芯。很怪,一支一支水烛举在蒲叶间,还闻得见浓浓的辛香味儿,这么多水烛压在枕头里,什么味儿也没有。好像,那股辛香就是生命的味儿。它们被折下来,挤压在一起,枕芯里盛放的变成无生气的物质,不是有灵的生命。它叫水烛,它一生必须被水所困,它端直举起的烛是棕色的,点不亮,也点不燃。我觉着它们像小犯人,被捆扎的又硬又直,风吹来,只能硬挺挺歪着身子摆。它不像老屋里的花树般的大草,伸枝展叶,挑满花穗,在风里自由的长,自由的摆,充实,得意,自在。我被伙伴们抛下,在野地里并不孤单。我躺着看云,云有天野,我有原野。云怀想闪电与惊雷,乐滋滋制造雨水,我一头扎进草木昆虫的领地,做个小心翼翼的窥探者,发现谜题,揭开谜底。没有什么能留住一朵云,也没有谁能留住我,我和云,都有一束自由的灵魂。云的灵魂已经开放,它以天为野,开出奔涌的山岭与兽群,开出温柔的波纹,开出风与光的逗引,开出暗淡与光明。我还小,将灵魂的花束抱在怀里,站在人与自然的边界上,左跨一步是拘谨与怯懦,右跨一步是原野的王。3.有一段小路,我每天都要走,一头拴着石箍窑里我的家,一头牵着学校。小路两边的草像疯了一样长,全都比我高。蒿子高出我两头,青蒿上有隐身的绿扁担蚂蚱。皱叶酸模更高,像高粱一样在顶端举一束长穗。连灰条条都长得超过我,叶背上的灰粉刷在衣衫上。苍耳个头和我差不多,探头探脑,将种子挂在我衣角。这些草各有各的味道,聚在一起,是潮的,是腥的,又是暖烘烘的,能把空气搅稠。在旷亮的野地里我是王,在被高草簇拥的小路上,我却失了气场。我人矮,胆也跟住矮,要是偶然落了单,更落魄成惶然小兽,眼睛四处斜觑,脑后全是动静,脖颈梗直,脚下生风,仿佛四面楚歌,险情暗涌,一路全是不祥之兆。真是不祥,且不祥之事接二连三,否则,上学路上我怎么会落了单?前几天,她们在班上密谋着什么。小孩子的密谋其实很可怕。她们装着保密,却故意漏出零星的话,翻着眼白将某个被密定的人多盯几眼。她们看起来都不是日子滋润的女孩,头发干干黄黄毛毛躁躁,脸上土缺缺的,裤子嫌短,上衣嫌长,裤子屁股上垫了布,缝纫机转圈走趟子,像操场上的跑道。她们在班上大几岁,又是各样游戏的能手,就占定了老大的位置。定夺妥了,被围在中心的那个高个子女孩手操在兜里,靠教室窗子站定。其余几个四散开,一个走到我跟前,说,从今天起,不许跟琴玩,否则小心着。我赶紧点头。我远远望着琴。我从前没注意过她,与她没怎么玩过,可她突然的被孤立,反倒让我时时观察着她。她站在双杠那里,她们赶她,她走开,走到单杠那里。她们又去单杠上折腾,照例呵斥她,她不回嘴,走到操场那一头,蹲在一个沙坑旁边。不管在哪里,她都朝着她们的方向,偷偷望着,似乎怕错过她们中谁一心软一招手,赶忙奔回去。她被抛开了,但她没有野地。不,她并不向往野地,她向往她们。我远远望着琴。望着她们。做了一个决定。我想,如果我走近琴,被孤立的就是两个人,我和琴。那么,即使没有野地,我不孤单,琴也不孤单。我向琴走去。那条路真长,比从家里到学校的被高草淹没的小路还长。所有的目光盯在我背上,她们往一起集中,把目光聚成一个榔头,砸在我背上。第二天,我上学的脚步几乎是轻捷的,我想,我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只有她,她只有我。到了学校,一进教室,我就望向琴。可是,琴,跟她们在一起,她们晃着脑后毛躁躁的辫子凑在一起密谋着什么,翻着眼白,咄咄的目光一闪一烁盯紧了我,这里面,也有琴的目光。我真正落单了,唯余野地。可是,不祥之事接二连三,还不算完。那天上午语文课安排了词语解释测试。老师在讲台上读出一个词,我们先默写出来,再解释它的意思。我不怕考试,尤其不怕考语文,最不怕的就是这种只靠记性就能应付的词语测试。老师把词语念完,漫不经心的在教室里来回踱步,我几乎和老师同步完成,草草检查一遍,颇有些得意,向后一靠,夸张地打着哈欠,前后左右张望起来。那一幕,我不该看见,不想看见,也不敢看见,可偏偏就看见了。她们中的两个,在老师擦身而过向后走去时,迅速翻出课本……我急忙收回目光,可窘急的她们几乎同时抬头,看到了我。下课了,我心神不定,预感到大事不好。果然,她们围过来,遮住洒在我头顶的阳光,不怀好意的吃吃笑着,枯黄凌乱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干草的光,她们搡我一把,说,"你赶紧去办公室,老师叫你呢!"我怀疑地看着她们,看着她们和琴,她们的眼睛里都扑腾着小兽,刚学会扑食的,见什么都想要咬一口的小兽。我的心智还不能判断她们在玩什么把戏,但已经察觉通向办公室的路暗无天日,又窄又长。我喊了报告,她们一起跟进来。还没站稳,瘦高个的女老师就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她尖利的嗓音因为极度愤怒变得嘶哑,她操着陕北口音的普通话冲我叫,"你这个小骗子,你小小年纪居然像狐狸一样狡猾!亏我一直当你是个好学生!"对面的老师那么愤怒,一句一句,像是扔石头。石头埋到了腿弯上,腰上,脖子上,脑袋上……把我都埋完了,她还在扔。她走过来,手放在我后脑勺上猛一压,"你竟然还抬着头?你竟然这样不知羞耻?我今天才算认清你了!原来你每次考试的好分数就是这样来的!"她冲到办公桌前,抓起我的默写本,嚓嚓撕的粉碎,狠命扔在我头上。她们站在一旁,装作俯首帖耳,她们中间,有控告者,有作证者,铁证如山。我垂着头,不掉眼泪,不认错,一声不出,看着默写本的纸屑从脑袋上往下掉,落在纽扣上、口袋沿上、裤腿的褶皱里、鞋子上。最后,老师锐利地喊一声,"你明天就把家长叫来让我见识一下,滚——"老师那样愤怒,愤怒到面孔扭曲,变腔变调。我走出办公室,想,她是哪个小孩的妈妈?我没有家长可叫。有家长我也不会叫。哥哥又病了,一病就朝不保夕,家里到处是血,炕洞门前的草木灰被血淌湿,簸箕里是浸透血的棉花棒,家里弥漫着血腥气。哥哥被带去兰州看病,我不能添乱。我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一个巨大的泥潭,想活命,就不能挣扎,不能呼喊,不能辩解,只能一动不动,安静地趴在上面,不让自己陷得更深。上课了,老师走进教室,她的目光像刀子,一下就把蜷成很小一团的我剜出来。她断喝一声,"你给我站起来!你好意思坐着吗?"我慢慢从座位上一点点升高,"我让你叫的家长呢?家长为什么没有叫来?"她一句接一句冲我扔石头,我铁定了心要安静地趴在泥沼表面,不叫喊,不挣扎,不吃饭,不喝水……她愤怒了,"你不要挡住后面同学的视线!站到过道上去!从今天开始,一天不叫来家长,就一天别想坐下!"我挪出座位,站在过道上。他们听课,我没听,我的心飞去了野地。他们写字,我没写,我的脚奔向了野地。他们下课出去玩耍,我不玩,我有我的野地。他们去上厕所,我憋住,我要去我的野地。有一天,哥哥终于好好的从兰州回来了。我扑过去,站在妈妈面前,先是呜咽,而后号啕。他们以为我想念她,没人懂我满腹冤屈。妈妈抚慰我,翻出一件新织的西瓜纹毛背心套在我身上,背心的颜色搭配得真漂亮,胭脂红与米黄色相间,穿在身上,我像个嫩生生的花骨朵。我被这绚丽打动,顿时忘掉窘迫的处境,欢天喜地换上新衣服去上学。站在教室过道里,我才反应过来自己犯了多蠢的错误。新衣服的颜色那么鲜亮,鲜亮的将小小的我放到无限大。我本该穿最灰暗的旧衣服,最好很久不洗很久不换,把自己融为其他同学衣服、书包、皮肤的一部分,像一只愣头愣脑的屎壳郎,从粪团里钻出来,也要在身上背几个小小的粪球。可是,我自己将自己推到一个无比显赫的位置上,供人一眼锁定。果然,在几个星期对我不闻不问之后,老师再次注意到我。她憋了一肚子话,她恨我不做声,不辩解,不掉泪,她一堆一堆向我扔石头,仿佛要用石头将我埋葬。终于,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我被逼出教室。我下坡,穿过场部,走到通往川外的大路上。汤土很厚,又虚又软,一踩一空,脚下腾起粉尘。我的鞋子被土淹了,半截裤腿被土淹了,越走越沉重,虚土仿佛有了吸力,每一步都要用力拔出来。天空上没有一朵云,云不忍心,所以,就躲了。离父母收获的田地近了,我停下来,眺望着……那是多大的一块地啊,割倒的玉米杆被立成圆锥状,像小小的草屋子一字儿排开。金黄的玉米堆在地中间,比黄金还要绚丽,比太阳还要滚烫。男人们一抱子一抱子把玉米杆拖到一起立起来,草屋子非常小,男人们更小,小到很可怜的样子。女人们坐在玉米堆里,用力搓着玉米粒,她们大半个身子都浸没在玉米里面,一大堆玉米就像一条铺开的长裙,只是,长裙上面,都是劳累而汗湿的脸。我在路上的汤土堆里站了很长时间,远远眺望着那些很小很小的大人,还有他们中间很小很小的父母亲,而后,我回转身,又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通往学校的小路两边,荒草怎么会长得这样疯狂呢?它们不屈不挠地探出手臂,每株草都想拽住我。它们一起喊,别去学校!草木间各样鸣虫也声嘶力竭地附和,别去学校!这天籁之声连成一片,万众一心,一同高喊,别去学校!前方有亮光,一闪一闪,是一根细铁丝。孩子们都喜欢恶作剧,细铁丝拴在路两旁的草杆上,变成一道隐形的拌索,那些快迟到慌里慌张的学生在小路上奔跑,多半能摔个狗啃泥。我站住,冷静地布置这道拌索,两端绑牢,我注视着这根在阳光下微微闪光的东西,一步一步后退,后退,后退……停下,起跑,向自己的拌索冲去。耳边是风声,脸上奔涌的,是汗水,还是泪水?我脚下一拌,身子向前扑出去……爬起来,检查自己的脚腕,没有受伤。我重新调整拌索的高低,再后退,再前冲……我一次又一次扑倒在地上,直到脚腕被铁丝挂的鲜血淋漓……我颓然坐在地上,看着自己的脚,胡乱抹着脸上的汗水,还是泪水?在草木间,我是被簇拥的王。为什么在同类的世界里,却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我想念祖母啊,想念祖母院子里那棵长成树一样的大草。它是草,却茎干粗壮,绿叶纷披,长成了树的样子。它用无数细碎的小花朵挤成一串串花絮。它模仿麦穗的充实,并叫这充实更美。它枝开叶散,自由自在,放纵舒张。它在秋季绚烂,让蓼风点燃河山。4.知道它的名字,已是成年之后。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祖母,失去了兄长,失去了老屋的大院子。我还,失去了野地。再见到它,在婆婆家的小山村里。我带着儿子,儿子的个头才齐我的腰窝。一户人家门口,老汉拿着砍刀,正准备将一株红蓼砍倒。儿子问,为什么要砍掉它?老汉回答,它长的乱七八糟,不好看,还占土地。随后,那一树红蓼躺在房后的破席片上。那竹席,曾经是粮囤的一部分。第二天,我们再去看它,它还未脱水,茎干铮铮,枝舒叶朗,花穗挑在骨节上。儿子问,它为什么还没有死掉?我说,因为它虽然是草,却更像一棵树,树都刚强,不会轻易死去。儿子问,它那么好看,老爷爷为什么还要砍掉它?我说,因为它太像一棵树,长得太自由自在,会遮住下面蔬菜的阳光,会占去一小块有用的土地。儿子问,它为什么是一棵草,不是一棵树?我说,草是它的命,它改不了。树是它的灵魂,它能活成它喜欢的样子。此后,我开始以文字与思想布阵,筑造城池和粮仓。并试图拥有,以诗性的词语摆布思想的神力,抛出一根根红蓼花穗般的绳索,从0到1,从至高到至低……我用词语拼合成墙垣,叫句子绵延成山峦,标点是人,是小兽,是低草与高木,是思想搭乘的飞鸟……纸上的城池,纸上的野地,纸上的粮仓,就这样用汉字的深情砌成。当我的城门洞开,汉字铺就的大河、山岭、草甸、海水一涌而出。谁蒙受了汉字的荣耀,即使是片羽之光,谁也会广阔无际。它叫红蓼。它低于黄土,高于塬畔,以草的姿态完成着树的使命,带着枝头绽放的荣光,带着一年坠落一次的绚烂与眩晕,以及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沉向大地的壮美……作者简介:
作家。陇原读书会发起人。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沉醉山野,倾听草木拔节、虫鸟叙鸣之声;沉迷文字,坐拥江河静阔、天地自在之境。识别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kelanga.com/mgzz/90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