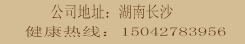、酸筒秆
我小时候眏(放)牛,有时看着它不停地吃,也不禁肚里馋虫大动,于是也会想办法弄点吃的。我和当时的小伙伴们,试吃过牛最爱吃的几种草,比如芦茅。这是一种类似于芦苇的长在山坡的植物,春夏青翠欲滴,秋冬枯黄萎白,但不管怎么样,它都是牛的最爱和首选。我也吃过它,当然是选春夏青翠的芦茅,剐去粗叶,一层层剥出白嫩的心茎,每根大约一寸长的样子,刚好一口咬下,慢慢咀嚼。感觉粉嫩生脆,开始会有一股淡淡的青草味,接着便嚼出甜味了,只是那甜味太短暂,没来得及回味,便咽下肚了。
还有一种叫马背筋的草,吃法与芦茅一样,味道也差不多,这两种要算是牛最爱吃的草了。当然牛还喜欢吃我们撒过尿的草,它只要看见你站着撒尿了,便马上蹭过来,迅速地把沾尿的草吃了。
放牛时最爱吃的要算是酸筒秆了。这是一种爱长有水边湿地的东西,绿色的叶,麻色的茎,高的能长半米,一般的也就二三十公分,抓住一折,它便嘣的一声脆响断了,掐去枝叶,然后小心翼翼地剐去薄薄的皮,便露出青白色的茎管来了(它是空心的),握着一口一口慢慢地嚼,一股沁凉的酸便溢满口腔。酸是酸极了,但还是要说它好吃。嚼吸过汁液之后,便将口里的渣吐出来,酸筒秆可是不能吞的。
吃酸筒秆的时候,往往是将牛赶到水沟里,让它一路往上或者往下吃草,我则踏在水沟岸跨上牛背,随手折下酸筒秆来,一边吃着,一边用小竹枝替它赶着牛虻。
那时放牛是农家孩子的必修课,我就放过好多回牛。我们生产队有黄牛和水牛,但孩子们喜欢放的牛,都是水牛,黄牛总是老人放。因为黄牛是很枯燥的一种牛,似乎除了吃草和耕田,其他的它都不会了;而水牛则节目多多,顽皮极了,它不但嗜水、好斗,而且还能和放牛娃交上好朋友——这点是很重要的,好比这条牛你放熟了,它就听你的,对你精心割来的青草,它狼吞虎咽地嚼着,不时对你投来感激的一瞥,这时一条庞大的牛,会让你觉得它温柔极了。关于放牛,有只童谣是这样说的:
谢家门前一树桃,
左一摇来右一摇,
摇落三十三只尖嘴桃;
大的吃哒放黄牯,
小的吃哒放牸牛;
牛啧牛啧跳过江,
吃哒对门一丘秧;
婆婆肩根棍,
公公肩根枪,
一夜赶到大天光。
不过坐牛还得有个诀窍,那就是得替牛赶牛虻,要不牛被牛虻咬痛了,前面一个甩头,后面一个抽尾,一不小心便顶到坐牛人的小腿了,或是在小腿上抽了一下,那是够痛的了。我们平时坐牛很少被牛搞到,但吃着酸筒秆就难免了。
后来看中药书,才知道酸筒秆还有一个药名叫:虎杖。能祛风除湿。
、耙茶子
我们乡下有句话,叫作“走路不弯腰,灶里没柴烧”,指的是一个人一定要勤快,做事要“奔身”,所有吃的喝的,用的花的,都在山上土里,但你得去把它们找回家,比如说深秋初冬的耙茶子。耙茶子和捡禾线与锄红薯一样,是指在生产队将油茶树的茶子采摘完后,去寻找那些藏在树叶间没被发现的茶子。
耙茶子分两次,一次是学校放假,规定每个学生交多少斤茶子,二是自己利用课余时间耙到的,拿回家的。因此一到耙茶时节,每家每户的小孩倾巢上山。我那时年龄虽小,但特喜欢做这个事。一大群小伙记们背着书包,每人手里拿着一个长约一米五的竹勾,欢天喜地上山了,在漫山遍野的茶树间,寻找被大人们遗落的茶子。
茶子一般在几个地方:一是高处的,主要是树梢,那得用竹勾一把勾住拉下,摘了,如实在太高,那便得爬树,山里的男孩个个都是爬树好手,更何况油茶树枝叶繁茂,好爬;二是低处的,实在太低,被權木遮蔽住了,没被大人发现;三是掉在地上的,油茶树下權木多,茅草多,大人在树上采摘,难免不掉一些。反正几场茶子耙下来,交满学校规定的那几斤茶子是完全没问题的,问题是如何耙多一点给自家榨油,而给自家榨油的那部分,决定一家后一年的生活质量,因为靠生产队分下来的那几斤油,是完全不够吃的,没有油了,就只能吃“白锅菜”、吃“盐抹汤”。所谓白锅菜,就是什么油也不放,用水将菜煮熟;盐抹汤则是一锅水烧开,撒上几点梅花盐,有斑椒的放几只斑椒,有豆豉的放几豆豉,但如果放了豆豉,那就不是一般的盐抹汤了,叫作豆豉盐抹汤,比一般的盐抹汤可高级不少。
但是孩子们也实在耙不了多少茶子,山就那么多,油茶树也就那么多,而孩子们却一年比一年多。要耙得多,有两种途径,一是家里的大人有私心,告诉孩子到哪去,然后他们故意留下一树或者一枝的茶子不摘,或是故意掉很多在地上;二是在采摘完生产队的茶子后,大人们到深山里去耙,那些深山里间或有几株野生大茶树,不归生产队管,谁耙到就是谁的。大人们惦记着,算好日子进山。
我们结伴耙茶子时,也念童谣,这童谣叫《大实话》:
桐籽打桐油,
茶子打茶油;
人在桥上过,
水在脚下流;
三个半壶壶半酒,
和尚庙里有;
板凳四只脚,
卦在神龛上。
区别于《大实话》的童谣也有一只,叫《扯炮歌》,常在念完大实话后念出来:
生我姐姐我摇箩,
收我姆妈我打锣;
出门撞哒牛打滚,
进门碰到马卸窝;
鲤鱼撒籽高山上,
风吹麻石滚上坡;
急水滩头鸟砌窝,
干塘浸死麻鸭婆;
和尚辫子就地拖,
从来不唱扯炮歌。
唱唱扯炮歌也算是耙茶中间的放松与休息,笑闹一阵后,感觉劲头又上来了。大人耙茶子可是喜欢唱山歌,尤其是那种刺激的。我们一帮细把戏都会来几只,只是不敢唱出来罢了,多少年后的今天,我还能依稀记起一些:
昨夜连姐去夜深,
走到姐家关了门;
走到前门击三掌,
起到后门咳三声,
叫醒姣莲快天门。
叫我开门就开门,
骂郎三句不是人;
君子约郎期下等,
未到日期胡乱行,
快快出去要关门。
要关门来就关门,
双脚蹿出姐房门;
过了高山有大庙,
只只庙里有观音,
观音比姐胜十分。
反手扯郎笑盈盈,
一句笑谈把做真;
下次总不笑哒你,
笑哒你来不是人,
红罗帐内赔小心。
这些山歌平时是不准唱的,但到了山上,尤其是面对这一片片丰收的茶子时,扯开喉咙唱一回,那是没有人管的。
耙完茶子后,要放到阳光下暴晒,直至茶壳全部干枯裂开,吐出黑色的茶子来,茶子的样子很像大蒜,大小也差不多,只是颜色不同。这时将茶子与茶壳分离,茶壳担回家放火塘边,那可是熏腊肉的好东西,熏出的腊肉有股天然的茶油香味;留下的茶子得继续晒,晒到嚯嚯作响,颜色变浅才收起,择日进油铺榨油。
由于父亲在外地上班,因此每年都没有耙到多少茶子,大多在晒干之后,过秤给了别人,别人在榨油后,再按比例分油给我家。但有一年耙了不少,是我父亲刚巧放假在家,整整耙了一担茶子。我问父亲怎么能耙那么多,父亲笑说,我耙了他们还没有摘的茶子!
不过,这也就不叫耙了。在我看来,耙的意思应该是像犁耙耙田一样,将山一遍遍的梳理,这事也许更适合孩子们。
、榨油饭
我们大队共有十七个生产队,可能有三四千人,但只有一个榨油坊,坐落在下铺,离小河不远处的田边。一条水圳从李家里前面的河堰一路走来,将河水引到榨油坊边,直冲筒车(水车),筒车转动,带动油坊里碾车转动。碾车由支架、碾轮、碾巢组成;碾巢是由几段宽沿尖底的轨道组成一个圆圈,生铁铸就,直径一丈有余,碾轮像是杠铃的铁饼,但边沿削尖、刃钝;一部碾车常用四个轮子,每个轮约二十斤,十字分布;轮与之间的距离足可架牛,当水力不够时,便用黄牛来拉。榨油坊另外还有两个重要部分,一是油榨,二是大灶。大灶上有大锅大罾,可炒可蒸;油榨则是用于榨油的,有巨大的用于撞击的木槌,和同样巨大的用于压榨油枯的楔子木。茶子进榨油坊,第一道工序是炒或者焙,然后碾末,然后蒸,然后扎枯上榨,然后便是出油了。
这样的过程本来也挺简单的,但不简单的,是那榨油饭。我们乡下有句俗话“三代做官,不可轻师慢匠”,不管哪家,有匠人进屋时,都得招待好好的,一是匠人会将手艺做到最好,二是也传出主家的名声。有个笑话,说是有个人家请篾匠,很刻薄,餐餐都是两只青菜碗,篾匠便没有将活干好,主家骂篾匠,“你瞎眼了”。篾匠回答说,“做的人是没有瞎眼哦,请的人才瞎了眼”。篾匠尚且如此,那榨油师傅可不得了了,他少撞两槌,你就不知道要少了多少油了。所以主家都是捧着给吃的,大鱼大肉的,肯定少不了,那菜里的油,更敞开着由你放,只要你吃得下。
那榨油坊又刚好在上学要经过的路旁,每次上学和放学,都能闻到里面浓浓的油香和菜香,一伙同学总要拐个弯进去看看,看看里面有没有熟悉的,或许可以讨一口好吃的呢。我也跟着去,但我家没有榨油的时候,也没有可以替生产队去榨油的劳力,所以我每次只是去闻闻油香,看看人家是怎么吃的。我最喜欢看他们吃大肉,切得一两寸厚、四五寸长的一块,煮得油水只滴,到口就溶,一大钵的,他们一下子便吃完了,把我看得口瞪目呆。而且他们还喜欢赌吃肉,一个人说他能吃多少多少肉,另一个说财着你吃,吃不完又怎么怎么的。一旦赌起来,便有许多人围观,可热闹了。
有时,他们吃饱喝足后,会有人挑起来唱山歌,这个我可喜欢听了,我记得一开始总是唱姣莲:
姣莲门前一丘田,
我郎批着作几年;
拿张镰铲去看水,
一打春锣二拜年,
心中有意看姣莲。
姣莲门前一口塘,
姐在塘边洗衣裳;
手捧擂槌将郎看,
十个指头捶五双,
这是想郎受的伤。
……每唱到这时,就有人提出来要唱点带劲的,于是唱的人也提出来,没有酒可唱不出来。最后总是喜欢听歌的人端来了酒,喝了酒的人咂咂嘴唇就唱了:
下昼日头往西斜,
乌油伞子斜斜遮;
一遮遮到姐身上,
二遮遮到我的他,
遮住我郎好采花。
好听的歌便这样起了头,接下来的,纯属成人歌曲,我们小把戏听不太懂,但也面红耳赤地听着。直到有个女人进来,骂,要死的,伢细的咯多,还好意思唱这歌!唱的人没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倒是不好意思了,背起书包,去学校。
我渴望着能吃上这样的榨油饭,但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便只有听听唱,打打眼睛的牙祭得了,有时也能在他们旺盛的火塘里,夹上几个木炭,放在自己的炉子里;碰到运气特别好时,也可以捡上一角碎茶枯,赶紧拿到门外,一溜烟跑了。当然有时也怅怅然的,无端想着乌油伞子斜斜遮……
、学打铁
我一直不会读书,在学校总是挨批、挨打、挨罚最多的那个,所以从小就恨透了老师,到现在对老师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我热爱劳动,上山下田,非常奔身,从不敢落后于人。尽管这样,家人还是说我懒,在那时乡人的眼里,作田是没有什么出息的,一定要会读书,跳出农门,所以只要不读书,那就是懒;而只要是读书,哪怕倒了扫帚也不扶,那也是勤快。如果不读书,另一个出息是学手艺。不管是木匠、篾匠、砖匠、石匠、铁匠还是剃头匠、杀猪匠、补锅匠,只要学出来了,也算是有了“养身艺”,哪怕做得再差,油罐子、盐罐子总能赚个满吧。如果连这个也不学,那才是真正的懒!乡下童谣是这样说的:
一家说我懒,一心学做伞;
做伞难斗把,一心学打卦;
打卦不顺手,一心学做酒;
做酒难和糟,一心学打刀;
打刀难打薄,一心学挖勺;
挖勺难挖空,一心学郎中;
郎中难看脉,一心学做贼;
做贼难挖壁,一心学打石;
打石难蹲久,一心学放牛;
放牛难割草,一心学剃脑;
剃脑难到家,一心学弹花;
弹花难打絮,一心学唱戏;
唱戏难唱生,唱得人发癫。
每次面对我不读书,父亲总是问我,那你去做什么嘛?我说去学剃头。父亲气得要命,说,剃头有什么好,油沫邋遢!我不吭声,父亲便又苦口婆心的劝我认真读书,仿佛除了读书,便没有了任何出路,当我好不容易混了个初中毕业时,父亲算是对我的学习之路彻底放下心来,他叫我去学杀猪,师傅都说好了,只差去,要不是母亲反对,也许现在菜市场的猪肉档上,多了个卖肉作家。
其实在我说学剃头时,心里想的,并不是剃头,我也觉得那个手艺不合适我,我想的是学打铁,只是父亲曾对铁匠作过这样的评价:打铁那可不是人做的,太辛苦了!我知道他会反对我去学打铁的,所以说学剃头了。剃头虽然油沫邋遢,但比起打铁来,要轻松多了。而且人人都有一个头,一年四季都要剃的,不愁没生意。而打铁就不同了,还有什么东西比铁的更结实呢?更何况一家又有几个铁器呢!
而我为什么喜欢打铁呢,我觉得这东西太神秘了,那么坚硬的一砣铁,想要它变成什么就是什么。有时我看到家里的什么东西坏了,就会想,要是铁打我就好了,我甚至幻想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铁打的,尤其是要打把超级锋快的钩刀,把对门岭、菜花洞里的柴,全部斫回家。说句心里话,我真正喜欢的,还是斫柴!
关于打铁,乡下童谣是这样说的:
东打铁,西打铁,
东家留吃饭,
西家留我歇,
我不歇,
我要回家打毛铁;
打把刀子快又快,
割哒婆婆九蔸菜;
打把刀子锋又锋,
割哒婆婆九根葱;
婆去告状,
撞到老和尚;
老和尚念经,
撞到观音;
观音打鼓,
撞到一只老虎;
老虎张口,
撞到黄狗;
黄狗打个屁,
打到你的肚子蒂。
戴斌年生于湖南平江,系中国作协会员,宝安区作协副主席。他有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大家》《长城》《小说界》等刊物发表,出版有长篇小说《我长得这么丑,我容易吗》等四部、中篇小说集《我们如水的日子》。戴斌在2年被评为“深圳市宝安区建区二十周年50名优秀人物”
印象平江县(yxpjx)合作QQ/
平江资讯·街坊爆料·交友聚会·商家美食·品牌合作
↓猛戳阅读原文即可进入最火爆的平江生活圈!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kelanga.com/mggs/91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