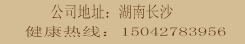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习性 > 当代笔记小说专题李永生故里奇谭四章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习性 > 当代笔记小说专题李永生故里奇谭四章

![]()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习性 > 当代笔记小说专题李永生故里奇谭四章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习性 > 当代笔记小说专题李永生故里奇谭四章
李永生作品《故里奇谭七章(外二章)》刊发于《大观·东京文学》年第1期当代笔记小说专题,现摘选四章。
故里奇谭四章
李永生
猫王
猫王不是猫,是涞阳一个卖鼠药的老头。
那时候,猫王六十多岁,家住涞阳城西二十里地的一个丘陵小村,一张圆圆的皱巴巴的大饼脸,细眼眯缝,长得有些随猫。猫王整天笑呵呵的,推车串村卖鼠药,逢涞阳城大集,便到县城角儿大街摆摊。
猫王不管走到哪里,都很热闹,屁股后边总跟着一群蹦蹦跳跳拖着鼻涕的孩子。人们喊:“猫王来了!”有人打招呼:“老猫来了?”老头呵呵笑着嗯嗯应着。猫王怎么那么招人?一是他装束古怪。头戴一顶猫头帽子,那帽子花花绿绿,猫眼猫嘴猫耳猫鼻子猫胡须画得栩栩如生,一张圆脸被帽子包裹起来显得十分滑稽。外罩一件画着黑斑纹的大黄罩衣,衣服后边还耷拉着一条软塌塌的大尾巴,还真的像一只古里古怪的大花猫。孩子们嘻嘻哈哈跑到他身后抓尾巴,猫王就故意和孩子们逗,玩转圈圈。二是他推的小车好看。猫王推一辆独轱辘小车,车上是座漆得五颜六色的倒凹字形木箱,木箱上几溜小抽屉,如同药店的药柜,上面还画了一幅老鼠嫁女图,一群老鼠抬着八抬大轿,一群老鼠高扬着卷曲的细尾巴排着整齐的队伍吹打各种乐器。车辕上绑着根竹子做的旗杆,上面飘荡的除了花花绿绿的旗子,竟还有两张风干的黄鼠狼皮子。猫王推起车子走动,就如同一座五颜六色的小房子移动过来。猫王还被人喜欢的又一个理由是他会说数来宝。“爬锅台上案板,踢烂盘子蹬烂碗;老鼠精老鼠能,不要梯子会上棚;喂个猪,喂个羊,总比养个老鼠强;吃了咱的老鼠药,先麻嘴,再麻腿,鼻孔眼里冒血水,大的吃了蹦三蹦,小的吃了就没命。”那时候,人们到涞阳城赶集,许多人就是特意带着孩子来看猫王的。
当然,猫王这样装扮自己最终目的是吸引人买他的鼠药。猫王的鼠药很灵,货真价实,老鼠吃了死光光。鼠药治鼠,猫也治鼠,猫和药都是对付老鼠的,在他这儿,猫也是药,药也是猫,这或许也是大家叫他“猫王”的一个原因。猫王的鼠药,用草纸包成小包,装在他的小抽屉里,三个小钱两包药,猫王从小抽屉里拿出药包,还要把包重新打开,用一根细细的牙签在一个小瓶子里一蘸,把牙签抽出来在细细的药末上弹两下,鼻子凑上来一闻,朝主家一笑说:“玉皇大帝下圣旨,老鼠马上要成仙,小磨香油喝二两,不白世间转一圈。”猫王每天都能卖出不少鼠药,虽说挣的都是小钱,但积少成多,猫王日子过得不赖。
不过,有一天,猫王遇到了麻烦。
那天,本来心情不错的猫王又来县城赶大集。不一会儿,见一个中年汉子吵吵嚷嚷朝这边赶过来。汉子撸胳膊挽袖子,到了猫王跟前先朝小车踹一脚,然后抓住猫王的脖领子,一个劲喊叫着让猫王偿命。
猫王蒙了,拱手问:“小哥,我怎的得罪了你?”许多人围过来劝阻。汉子虽然被人拉开,但仍吹胡子瞪眼,一个劲要猫王赔命。猫王仍是一头雾水。周围人不停地劝,汉子这才降了些火气,磕磕绊绊把事情说明白了。
原来,这汉子的媳妇和他闹别扭,一时想不开,买了猫王的耗子药喝了,死了。
猫王叫屈:“鼠药药老鼠,她又不是不知,是她自己寻死,与我何干?”众人一听,都为猫王叫屈。但汉子是个混不吝的主儿,容不得讲理,非要拉猫王到县衙说理。猫王自知占理,就要随他见官,但好心人却劝:“现在是打官司的世道吗?任凭你再有理,不让你破半个家业脱三层皮,你能赢?不如破费一些,息事宁人。”
猫王觉得有理,托出个中人与那汉子商议,最后答应回家取十两银子给他,汉子才罢休。
猫王一朝被蛇咬,有了教训。自此再有买鼠药的女子,必先察言观色,若是愁眉不展或神情恍惚的,一律不卖,后来干脆不卖给任何女人。这样一来,他的顾客就减了不少,生意大不如前!
那阵子,猫王很苦恼。
过了些日子,猫王心情刚有好转,忽然一个消息像冬天的小北风一样嗖嗖钻进了他的耳朵——知县夫人也吃了猫王的鼠药。
猫王傻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他依稀记得前两天确是有个衙役买过他的鼠药,那衙役还是距他家三里地的同乡。衙役因为和他熟,还开玩笑说衙门里的老鼠胆子大,都跳到县大老爷的床上啃被褥去了。猫王还记得因为是衙门用,就没敢收钱,几包鼠药白送了。
猫王揉了揉麻软的双腿,手忙脚乱地收拾摊子,推着车回了家。
一连几天,猫王躲在家里胆战心惊,老妻试探着出主意说:“虽说吃了耗子药,但到底死没死还没弄清,不如托人打探一下。”猫王泪眼望着老妻,说:“如果没死,咱多出些银子,或许县大老爷会饶了咱们。”
猫王就拎了包点心去找那个买他药的同乡衙役。那衙役告诉他,由于抢救及时,夫人好歹保住了一条命,可是变得傻乎乎的,大概是烧坏了脑袋。猫王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百两银子掏出来,托他转交知县,又单拿出二两给衙役吃茶。然后心里七上八下地在家等消息。
第二天,衙役把银子退回来了。
还没等衙役说话,猫王哭了,说:“知道县太爷嫌少。”就又给衙役加了五十两,给他的茶钱也加了二两。衙役接过银子,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
转天又给退回来了,猫王这下更是六神无主。
猫王答应继续凑银子,让衙役回家等消息。衙役走后,猫王越想越怕,他不知道县太爷胃口到底有多大,但他也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银子,一着急,吃了自家鼠药自尽了。
其实这个刚到涞阳上任没多久的知县除了好色,也不是有多坏。他因为讨小妾惹得夫人喝了鼠药,多亏丫鬟机灵及时打翻了药碗,夫人只是喝进去一小口,一碗咸菜汤灌下去,就全吐了出来。当衙役拿着一百两银子来的时候,知县说了句:“与人家何干,退回。”
衙役也不是有多坏,那一百五十两银子他一两也不敢动,他这么做,也只是为了让猫王多给他加几回茶钱罢了。
没有猫王的日子,涞阳大街显得冷清了许多。
画匪
一不小心,吕四老爷被金华山的土匪谢老鸹绑了票。三个时辰前,管家带着一千块袁大头上了金华山赎票,和他见面的是土匪窝二当家的,二当家的望一眼摊在地上白花花的大洋,用脚尖朝管家的屁股点了一下,朝隔壁一个黑咕隆咚的小房间一努嘴,坏笑着说:“别弄一身臊气。”
管家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但当他见到吕四老爷,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臊烘烘的味道时,才明白,老爷尿了裤子。
管家怕土匪反悔,背上老爷慌慌张张出了匪巢。管家双手兜着老爷的大腿根儿,感到湿漉漉的。车夫远远瞧见管家背着老爷过来,赶紧掀起轿帘,帮着管家把老爷放在车上,放下轿帘,一甩鞭子,马车轰隆隆跑了起来。
这时候的管家,认真地看了看歪倒在被褥上闭着眼睛的吕四,小心翼翼地问:“老爷,他们没难为您吧?”
管家抻着脖子挨近吕四,给他把被子盖在身上,那臊烘烘的味道便更加浓烈地扑过来,管家想掩一下鼻子,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妥,便顺势给老爷掖掖被角。老爷的身子随着马车的颠簸晃动着,管家见老爷没搭话,害了怕,把手指凑近他鼻孔去探是否还有呼吸,这时吕四突然睁开眼,撩起轿帘往外瞧,管家忙说:“老爷,咱们出来有一会儿了,放心吧,离谢老鸹远了。”吕四长出一口气,整个身子瘫在被褥上,却又从鼻腔里哼出几句:“妈的,在涞阳县,老爷我这辈子怕过谁?”管家心里一乐,他当然知道老爷是个爱面子的主儿。吕四提高声调说:“狗日的谢老鸹。”管家随着接了下句:“落到我手里,剐了他。”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但吕家上上下下都还没睡,都在心急火燎地等待。管家把老爷背在身上进了门,大伙赶紧围上来。管家吆喝一句:“快烧热水,老爷要洗澡……”忽然觉得不该这样大声吆喝,便又把声音降低对太太和姨太太们说:“老爷不小心,弄脏了衣裳……”
吕四老爷洗完澡,又吃了一大碗荷包蛋,睡下了,半夜里却又被噩梦惊醒了几次,第二天日上三竿,才从被窝里坐起来,把一家老少叫到跟前。吕四老爷披着被子盘腿坐在炕沿上,咬着牙说:“谢老鸹,狠哪!我见着他时,这小子正喝酒,一盘子圆滚滚的眼珠子,蘸酱吃。没见过阵仗的,敢被他吓死。可我老吕,不怕他,我还想跟他要碗酒喝呢!”太太吓得吐出舌头,说:“谢老鸹长啥样?”老爷“哼”一声:“恶人自然恶相。”二姨太抢话说:“说不上青面獠牙,也是凶神恶煞!”老爷“嗯”一声,算是对这话的认可。
吕四老爷对谢老鸹自是恨之入骨,他决定,今年的“立春大考”,画谢老鸹。
立春大考,是吕四老爷的创举。少爷小姐加上孙辈二三十口,吕四很重视对子孙的教育,请私塾先生教孩子们读书,不论男孩女孩,都学习琴棋书画。为了鼓励孩子们学业进步,每年立春这天,便让孩子们展示一下才艺,比一次书画本事。到了那天,吕四亲自当主考官,哪个孩子考了第一,会奖励一个分量不小的金元宝。吕四给这起了个很大气的名字:立春大考。他说:“朝廷有秋闱大比,我有立春大考,如今科举废了,我吕家又把朝廷科考接上了。”
过去吕家的立春大考,是不设置主题的,任由少爷小姐们自由发挥,想画啥画啥,想写啥写啥。上次五少爷画了张“屎壳郎滚绣球”,画面上,一个黑色的屎壳郎正在滚动一个比它身体大好几倍的五颜六色的彩球。吕四说:“小五这画画得好,都知道屎壳郎滚粪球,小五能把粪球变成绣球,想象力蛮丰富!”那个金元宝就奖给了五少爷。
转天,立春到,吕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孩子们个个欢天喜地,一心要挣这个金元宝。管家一大早就吩咐下人们把几十张桌子在院中摆放整齐,上面铺好了笔墨纸砚和各种颜料。时辰已到,孩子们各就各位,开始画土匪谢老鸹。
吕四老爷端坐着笑眯眯地看着儿孙们舞文弄墨,时不时地走下台阶,挨个看看,或者朝哪个小姐点点头,或者摸摸哪个少爷的后脑勺以示喜爱和鼓励。
比赛结束,吕四老爷和太太姨太太媳妇们挨个品评。
几十张谢老鸹画像,或是满脸络腮胡子,或者血盆大口,或是拧着眉毛瞪着眼,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五少爷画得最狠,把谢老鸹画成了独眼龙,正张着大嘴,把刀尖上叉着的眼珠子往嘴里送。吕四老爷不住地点头,太太媳妇们也不住地议论,“这张好,够凶”,“这张更好,要吃人的样子”。
只有七岁的孙少爷久儿和大家画的不同,他画的谢老鸹,面白无须,还长着一双丹凤眼。大家一看,都笑了。太太说:“小祖宗啊,你画的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吗?”
孙少爷的母亲把画拿起来笑着说:“大家看哪,老爷让孩子们画凶神恶煞的谢老鸹,可久儿天性善良,心里就没有邪恶和丑陋,该好好保护和鼓励呢!上次老爷把金元宝奖励小五,不就是他把粪球画成绣球,把丑陋变成美丽,才惹得我们高兴吗?”
大家压根没想到她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一个个面面相觑,竟不知道说啥好。
吕四老爷哈哈一笑,连忙说:“说得好,说得好!”
那个惹人眼馋的大元宝,就奖给了久儿。
其实吕四老爷心里明白,虽然他最宠这个孙子,但这个决定一点儿也没有偏心的意思。他在匪窝,压根没见到匪首谢老鸹,只见到了二当家的和几个喽啰,谢老鸹多高多矮多胖多瘦多丑多俊,他压根不知道。他之所以把谢老鸹说得那么凶神恶煞,不过就是让大家增添对土匪的憎恨和惧怕,增强防范意识。还有嘛,万一有人想起他吓出来的那一裤兜子尿臊,也会觉得情有可原呢,毕竟,匪首谢老鸹不是一般的凶狠!
嫁妆
九姑娘嫁到申家的时候,那丰厚的嫁妆,令人咂舌。
九姑娘的娘家门第显赫。祖辈出过文秀才,也出过武举人,到九姑娘这辈,她的两个哥哥现在就在张大帅跟前效力,一个当旅长,一个做团长。
先前,申家托媒说亲的时候,九姑娘爹娘犹豫过。申家是涞阳大户,申公子当时十八岁,风流俊雅,又念过洋学堂,九姑娘全家都满意。尤其是九姑娘,也是念过洋学堂的,就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如意郎君,自打见过申公子,心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但爹娘有些怵申家老太太,申少爷的父亲死得早,现在是老太太当家。申老太太也是名门闺秀,她爹是武将,当过北伐军的团长。申老太太脾气大,打小喜欢舞枪弄棒,会打盒子炮,功夫得家父真传,即便到现在五十岁的人了,吼一嗓子仍能镇住一片。九姑娘爹娘就怕女儿嫁过去受婆婆的气,挨欺负。不过,既然女儿一百个愿意,申家最终答应了这门亲事。
申家合计,九姑娘的陪嫁一定要丰厚。姑娘出嫁,嫁妆好赖那可关系到门面,谁不是看人下菜碟?寒酸了在婆家会觉得低人一头,甚至一辈子被人轻贱,而丰厚的嫁妆,自然让新媳妇高人一等。嫁妆,关系到一个媳妇未来的命运呢。
况且九姑娘要嫁的是申家,而申家又有那么个强悍的老太太,一定要在气势上先压住申家。只要是能想到的,都置办了。美人榻、罗汉床、杭州真丝面双铺双盖被褥、西洋穿衣镜、镀金小座钟、铜蜡扦、白瓷茶具、挂镜挂瓶、金银首饰、珊瑚玛瑙,连刚时兴的留声机也备了一台,足足装了十辆马车。其实,九姑娘对这些不是多么看中,倒是那几百本她平常读的书,一本也舍不得丢在娘家,她把书装进两只大木箱,也当成了嫁妆。两个在军队里当官的哥哥觉得还不够牢靠,便以“保境安民”为借口陪送了妹妹一挺机关枪,并派一个班的士兵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送亲。
结婚那天,送亲的队伍和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朝新郎家浩浩荡荡进发。围观的乡邻很多,人们看新郎,也交头接耳议论轿子里的新娘子是怎样的妩媚动人,但更多的还是把目光投向那挺披红戴花的机关枪。那机关枪就支在第一辆车的木箱上,乌黑的枪口斜指着天空,威风凛凛地显示着它战无不胜的骄傲。那些大兵们,虚晃着马鞭吓唬围观的人们:“别挡路,叫你别挡路,机枪不长眼。”
队伍拐进申家大院,高高胖胖的申老太太以及所有的宾客都在兴高采烈地等待。新娘的嫁妆一件件行云流水般搬入洞房。最后,只剩下那挺机关枪留在车上,大家觉得把这个凶巴巴的东西放在温馨的洞房里终究有些不妥,但又不知道应该摆放在哪里。
开始拜堂了,申老太太端坐在太师椅上,接受了儿子媳妇的叩拜。司仪“送入洞房”的声音一落,早已按捺不住的申老太太便踮着双小脚快步走向那挺机关枪,一下抄起,把枪口对准了天空。
院子里的人一见这阵势,吓得纷纷退后,大家以为老太太要“哒哒哒”打上一梭子。只有九姑娘的两个哥哥和几个大兵不以为意,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为了安全起见,机枪弹夹里压根没上子弹。老太太比画了一下子就把机枪放下了,呵呵笑着说:“这大喜之日,哪能动枪弄炮!”老太太拍了一下枪把,赞叹道,“这玩意好,带劲。”
送亲的九姑娘家人这时开始琢磨,光知道机关枪厉害,想震住点儿什么,可是,这是不是反而让老太太多了个趁手的家伙呢。
人嫁过去了,九姑娘家里时不时派人打探消息,传回来的话都是“婆媳和睦,姑娘好着呢”,大家的心才踏实下来。
其实,申老太太也的确想给儿媳妇一个下马威的,只是她不管怎样刁难,知书达理的九姑娘都能够应对自如,把话说得丁是丁卯是卯,把事做得方是方圆是圆。申老太太觉得,儿媳妇手里就像捏了根绣花针,时不时在她的肚囊上轻轻点一下,那股火气竟慢慢泄了。
阳光好的时候,九姑娘把从娘家带来的两大箱书拿出来晾晒,以防虫蛀或是受潮发霉,然后分类整理。这时候,老太太往往也正坐在院中的太师椅上打着盹晒太阳。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媳妇蹲在那里把那些宽宽窄窄的书摆来摆去,想:机关枪和书,两样嫁妆,哪样更厉害呢?
街坊四邻们和申老太太一样也在琢磨,起初,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那挺机关枪,后来大家又说起申家儿媳妇那铺了一院子的书。
人们说这话的时候,刚刚过完蜜月,本就不想憋在大宅门里浪费青春的九姑娘和夫君双双到涞阳小学教书去了。
洋落儿
狼不吃是个苦命孩子,十岁时死了爹娘,吃百家饭长大。人说这种孩子,走两个极端,将来不是忒好,就是特坏。好,能成社会贤达甚至封王拜相;坏,会坏得没边,千人戳万人恨,死后不留全尸。
狼不吃属于后者。
狼不吃自然不是这人的真实名字,百家姓没有姓狼的。但大家都叫他狼不吃,真名叫什么,甚至姓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人一辈子和狼有缘。
三岁那年,在门口玩尿泥的时候被一只母狼叼走了,幸亏被及时发现,大家吆喝着拼命追赶,筋疲力尽的母狼才丢下他夹着尾巴跑了。
十几岁的时候,被一只饿狼偷袭过。那老狼受过伤,嘴巴大概是被“鸡皮炸药”炸过,只剩下一个上嘴茬。鸡皮炸药,是我们这一带猎人常用的土炸药,把炸药用鸡皮包裹,野兽贪吃去碰,就炸响。当时,那只狼从后面悄悄扑向狼不吃,把一双大爪子搭在他双肩。这是狼惯用的手段,只待人一回头就一口咬住脖颈。狼不吃果真下意识地回了头,也多亏那狼是半个嘴茬,想咬他没咬住。狼不吃一激灵,急中生智,双手攥住老狼的爪子向下一拉,脖子一挺,脑袋顶住了狼的下巴,就这么硬生生地把一只大活狼给背回了家。两个腿肚子被狼的后爪抓挠得血糊糊的。也就是从那天起,大家给这个人起了绰号“狼不吃”。
狼不吃走邪路,小时偷鸡摸狗,长大坑蒙拐骗。再后来竟干起了偷坟掘墓的勾当。
盗墓分两种,一为“干湿活”,一为“干干活”。所谓干湿活,是指盗新坟。干干活,指盗古墓。狼不吃“干”“湿”活都干。为学习盗墓的技艺曾专门拜过师傅,技术很好。起初,他兔子不吃窝边草,专跑到外地做活。后来贼性越来越大,就什么都不计较了,在家门口也作案。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防着他。谁家死了人,棺材里如放了贵重随葬品,为了蒙骗狼不吃,出殡前儿女们总要哭喊几句:“爹啊,你这么心疼我们,死了也不带一件东西走啊!”或者:“娘啊,你咋这么命苦啊,就那么干干净净地走了啊!”为了争取更加真实的效果,嫁出去的闺女还要和哥哥弟弟们演双簧,“啪”,脆生生地扇“不孝儿”一个嘴巴。
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老在外边跑总是不太平。狼不吃消停不少。日子也就过得寡淡。
三天前,国军和日本鬼子在距我们村十里远的大叉子沟打了一仗,双方死伤惨重。双方都还没来得及收尸。狼不吃听到这个消息,就想去那里捡“洋落儿”。这是个大活儿,为了让自己的胆气更壮一些,先是找了个小酒馆闷了三两“涞阳小烧”,然后打着饱嗝,一步三晃连夜奔了大叉子沟。
狼不吃一踏进大叉子沟地界,就闻到了一股死尸的味道。这味道对于常人来说,无疑是恐怖的。但狼不吃闻到的却是一股“肉香”,竟还使劲吸溜一下鼻子。
死尸横七竖八。
狼不吃目光贪婪。
狼不吃使劲呼出几口酒气,开始干活。他借助朦胧的月光挨个搜寻鬼子兵的尸体,很快从一个鬼子兵的兜里掏出一盒火柴和半包香烟,他擦燃火柴点着香烟,美美吸一口。他想,钻墓里能把人憋死,还是这活儿好啊,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这时酒劲刚好上来,狼不吃更加兴奋,他做了几个扩胸动作,若不是怕把狼招来,甚至还想唱上几句《盗御马》。狼不吃歪叼着烟卷,又把一个趴着的尸体翻过来,找出一沓钱。狼不吃双眼放光。接下来,狼不吃又搜寻到不少钱票,还有饼干、香烟、怀表,外加一面小镜子和一个花花绿绿的画本。狼不吃干得热火朝天,累了,就坐下来抽支烟,点着火柴翻那画本。
这时,他忽然看见不远处有条毛围脖。醉眼迷离的狼不吃以为看花了眼,揉揉眼,仔细一看,的确是一条毛围脖。狼不吃乐了。这样的毛围脖他看见过,大户人家的老爷少爷都喜欢戴这个,值不少钱呢。这种毛围脖有些还是用整张狐狸皮做成的,狐狸嘴还咬着尾巴根,就像一只活狐狸抱着主人脖子睡大觉。狼不吃纳闷,他是见过鬼子兵的,可从来没见过他们戴毛围脖,呼搭呼搭围着他们脖子的只是军帽上的三片屁股帘子。狼不吃想不明白,但既然想不明白就不想了,想那么多干啥呢?狼不吃刚要走过去,忽然发现那毛围脖动了一下,而且不是一条,竟是好几条。
母狼和她的几个孩子,本来正在欢快地觅食,没想到忽然遇到这么个浑身酒气的人。母狼望望狼不吃,又环顾一下自己的孩子们,几只小狼静静地围在母亲身边,一起摇晃着“毛围脖”,仰头看狼不吃,狼不吃眼前便晃起了十几盏蓝幽幽的小灯笼。
当然,尽管狼不吃喝得糊里糊涂,但还没有达到连狼也认不出的程度。如果放在平常,狼不吃再胆大,也会吓得屁滚尿流的。但今天,他竟忘乎所以地没拿这群狼当回事。
倒是那母狼,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或许怕和眼前的醉汉折腾起来伤了自己的幼崽,竟摇动一下“毛围脖”,对他置之不理,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继续带着狼崽子们在尸体上寻觅。
狼不吃却急了,那些鬼子兵兜里的饼干肉罐头,他还没掏净呢!还有那些钱票,可别被狼崽子们咬坏了。不行,得把它们轰走。狼不吃摸黑寻了块石头朝狼群砸过去……
至于后来怎么样——人若贪婪到与狼争食的程度,能有好果子吗?
作者简介
李永生,河北涞水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刊于《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天津文学》《读者》《故事会》等刊。获吴承恩文学奖、《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荷花淀文学奖特别贡献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在《保定晚报》开办《故里奇谭》专栏。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日文介绍到国外。著有《墨药》《儒匪》等小说集多部。
聂鑫森笔记小说四题
杨小凡:无味斋酒话四题
谢志强:江南聊斋四题
相裕亭:盐河旧事四题
王往:平原诗意四篇
曹洪蔚:汴梁物语四题
《大观·东京文学》投稿邮箱
小说:daguanxs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kelanga.com/mggs/51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