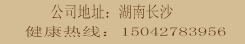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繁衍 > 流浪的中国人疫情下的菲律宾游记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繁衍 > 流浪的中国人疫情下的菲律宾游记

![]()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繁衍 > 流浪的中国人疫情下的菲律宾游记
当前位置: 屎壳郎 > 屎壳郎的繁衍 > 流浪的中国人疫情下的菲律宾游记
一夜之间,我们成了被嫌弃的人
1月20日晚上,落地马尼拉,老爸刷着手机,一声惊叹:钟南山院士确定新型冠状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这事儿大了!起初我不懂为什么人传人事儿就大了,又能有多大。老爸曾是呼吸内科专家,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国内也刚刚开始从上到下补充对疫情的认知碎片,段子和严肃报道齐飞。老爸老妈一辈子从医,对新冠有作为公民和医者的双重忧虑。往常的家庭旅行,一年不见的我们仨总是话特别多,凑在一块儿胡天海地大聊特聊,今年从出行第一刻起,他俩几乎再也没有放下手机,只要得空,就眉头紧锁,各自抱着手机窝着刷刷刷,叹口气,再继续刷刷刷。再揪心再牵挂,和国内终究隔着一道海。阳光烤在皮肤上暖洋洋,把思绪也拖得慵懒缓慢,五颜六色的小鱼儿在珊瑚里悠闲穿梭,国内的焦虑隔着手机飘来,多少滤掉些许切肤之痛,威力也减弱几分。出海,回酒店,看手机,无话。一天一天,时间刷得飞快。然跑得再远,震荡虽慢,终究不会缺席。从1月26日开始,一切都变了。1月26日晚间,香港政府以新闻稿的形式公布:从27日零时起,除香港居民外,所有湖北省居民以及任何过去14日到过湖北省的人士将不获准入境香港,直至另行通知为止。我们原定返程经香港回广东,第一时间看到这条新闻时,并没有引起我的警觉。我们早年在湖北出生和生活,后赴他乡筑起新家,户籍早已迁出,想当然算不上“湖北居民”。生活继续,一切如常。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我抱着一颗椰子平躺看海,懒洋洋地思考节后复工的事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妈妈的护照申请时间比较早,当时是湖北签发的,好像严格来算,是打了个“湖北居民“的擦边球呢!顷刻清醒,手忙脚乱查阅官方指导意见,翻遍全网,除了以上这句笼统的话,找不到任何执行细则,无法求证香港官方如何定义”湖北居民“,糟心。官方信息的模棱两可是日常熟悉的常态,此路不通时,民间散装信息雷达迅速上线。求助万能的朋友圈,请朋友们帮忙打听近期过关的真实案例,很快,大量二三度关系圈的湖北朋友们出入香港境真实案例涌来:据前线肉身实报,入境处官员在具体执行这项规定的时候打击面颇广,不仅直接拒掉所有湖北签发的护照,就连在湖北出生的人也要进小黑屋。总之,只要护照上出现“湖北”二字,不管什么情况,都被视为瘟神,拒之门外。紧急时刻,简单粗暴一刀切最为高效。宁可误伤一千,不能放过一个。我虽勉强理解港府的无奈,被官方正面嫌弃的感觉总是让人不快。好吧,生于湖北,是我们的错呗!政策条文不明不朗,既有误伤空间,自然也有申辩空间。香港本地朋友们非常热心地帮我打了很多咨询电话,建议我们试着在入境时解释,或能顺利通行。换位思考一下,去别人家里做客,身份不清不楚,确实给人添麻烦。距离回家时间还早,还是,改票为敬吧。发出求助信息之后,不少香港本地的朋友一直在帮忙查阅资料、打电话和加油打气,心里很暖鄙视与被鄙视
疫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信任链条的崩坏
很快我就明白,试图通过抠字眼把自己和湖北划清关系,在如山倒的疫情大势下,几乎是无病呻吟。短短几天时间里,我看到信任链条在雪崩——从对武汉人不信任,到对湖北人不信任,再到对中国人不信任,继而对所有身边的人都不信任。还记得我们旅行的开始也是武汉封城的伊始,封城令的副作用,是直接把已出城的武汉人架上道德的烤炉,一时间,网上关于“逃跑的武汉人”段子满天飞。中国人过年多少得整点仪式感。我们上岛最惦记的一件事情,是去找一家中餐馆订年夜饭。收完我们这桌的定金,餐馆老板掩饰不住生意兴隆的喜悦:订满啦,安排完你们这桌就收工,不再接更多的预订啦。喜欢凑热闹的中国人第一次对热闹产生了不安。思前想后,还是忍不住小声问老板:请问之前来订年夜饭的,可有武汉人?老板很无奈:听口音倒是没有,可咱也不好意思问呀,问出来是不是就算歧视了?旁边另一桌客人赶紧补上:现在哪还顾得上歧不歧视,我们可不要和武汉人一起吃饭,武汉人要是有点自觉,就不该出来给别人添堵。听闻大人们聊天,小孩子们的表达更是简单直白,用勺子敲打起碗盘,大声抗议:妈妈,不要和武汉人吃饭,我怕!我心里有点难过。这当然是歧视,武汉人错在哪里呢?可扪心自问,我也怕呀,把害怕表达出来的人,又错在哪里呢?还来不及细思这其中的微妙之处,随着疫情如泥石流一般推进,对武汉人的警惕就迅速扩展到了对所有中国人的警惕。旅行之初,从马尼拉到爱妮岛,机场里还只有少量中国人戴着口罩,一本正经严防死守的姿态和松弛的本地人相比显得十分可笑;一周后,从爱妮岛回马尼拉,机场里%的工作人员和30%的西方面孔也带上了口罩。值机柜台的小姐姐看到我们拿出7本中国护照,眼神明显一抖,第一句话不是SOP里的“您是否托运行李”,而是问您的身体怎么样?需要医疗救助吗?您……确定吗?口罩后的西方面孔明显在逃避口罩后的东亚面孔,整个脸被遮住大半,眼神和身体写满了“这儿为什么有如此多中国人,好可怕!”。这状态不稀奇,现场的中国人见到自己同胞都想逃。若不是狭小的候机厅和机舱强行把大家强行按在一起,每个人恐怕都希望和他人保持足够远的距离——此时,菲律宾仅仅只有1个疑似病例。入住马尼拉酒店后,酒店派工作人员每天4次入房间给我做体温监控和血氧检测,紧张得不太正常。我已习惯一路对待中国面孔的特殊待遇,亦想自证清白,就当免费身体检查啰,听之任之。原本安排大家在马尼拉游玩一天再回国,父母踏入酒店房门后当下就决定留宿房间不再出门,原来被菲律宾人恐惧的同时,他们同样恐惧也本地人:菲律宾的医疗体系并不十分令人放心,谁知道出门会不会有风险,人生还长,不差这一天游玩。我有点无奈。逻辑没毛病,只是我们终究不可能永远把自己和全世界隔离开来,直到病毒消失殆尽的那一天。理论上来说,病毒可能会被控制,但永远不会彻底消失,我们总得找到方法与之共处。道理是这样,情感上……算了,安全感是一门玄学,没办法,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吧,天塌下来,回国再说。在旅行途中,我们无意间因为中国脸成为行走的恐慌源,但幸运的是,菲律宾疫情很轻,华裔很多,始终并没有遭遇直接歧视,遥远的欧洲则陆续传来零星辱骂华人和直接针对华人的过激言行。光天化日之下没什么新鲜事,最初砸向武汉人的谩骂,将陆续一条一条砸到所有华人身上。武汉人、中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普通民众其实都是疫情的受害者,相比疫情,更难战胜的恐怕是仇恨和心魔。对于早就持有民族偏见的少数人来说,现在正是他们撕开政治正确的压制宣泄情绪的好时机。毛爷爷教导我们,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发出自己的声音,平衡信息对称,让更多深陷恐惧的人了解病毒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牺牲和努力,是每个海外华人的义务。春节假期结束后,我即将返回德国上班,我想,对于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我已经做好了尝试修复信任链条的准备。魔镜啊魔镜,请告诉哪里能买到口罩?
魔镜应声碎裂,卒
菲律宾许多华人超市已要求佩戴口罩才能进入点滴的担惊受怕汇聚成惊弓之势,裸露在空气中的呼吸道让人焦虑,无比焦虑。虽然菲律宾远离主疫区,为了我们过于敏感的小心脏,必须把配口罩提上日程了。第一天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就已经为时过晚,海外口罩已全线断货。早在疫情刚刚显露出虎狼之势的时候,我就和朋友一起,在欧洲亚马逊好一阵买买买,调一万多只口罩物资支援湖北,还因下单过多过频被亚马逊判定账号被盗,申诉了好一阵子。当时海外华人都在扫货支援国内,没几天,当时还一个确诊病例都没有的欧洲,在亚马逊上就已经买不到口罩了。菲律宾也是。我们一路都在买口罩,见到一个药店就跑进去问,从小众爱妮岛到首都马尼拉,几十家药店走下来,得到的回复全是口罩早已断货。马尼拉街头人们戴口罩的比例目测已经超过40%,人家都带着口罩悠闲逛街,我们却怎么都买不到,不停吃闭门羹,觉得自己特废柴。这事儿不合理。冷静一下,问自己:疫情的新闻刚刚席卷菲律宾不久,本地人第一反应就是去身边的药店买口罩,临时没有货很正常,但是,谁的信息会更为前置,谁的商业直觉更为灵敏,谁有可能提前屯口罩加价卖出呢?必然是我亲爱的同胞了。放弃本地药店,直奔社区华人超市,果然看见一箱KN95放在地上待售。一箱目测三百只,单价32人民币一个,够狠。考虑国内口罩更为缺货的现实情况,我本想跟老板谈个好价把一箱全部扫走,想到自己寻口罩的辛苦,算了,积点德给别人留点儿吧。买走40个,离开前顿了顿,折回来和老板套了套近乎,留下联系方式以备反悔,没准再过两天,32也买不到了,备个有用的线索总没错。出生于物质丰沛的时代,囤积居奇于我而言是个历史书里才出现的名词。中国口罩年产量45亿,已达到一个接近过剩的数量级,遇到黑天鹅事件同样在一夜之间无货,甚至引发全球断货,令人唏嘘。很多人在苦苦寻货不得时都发出类似的天问——口罩究竟都去哪儿了?短期供求的剧烈变动叠加春节期间产能停滞自然是引发口罩荒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经济发展至今,物质积累至今,已积攒起强国自信,可遇到灾难时,人性的恐慌互相加持,似乎仍然处处脆弱,打得人措手不及。我看到许多行业的供给侧上下游企业都在反思各自的产业布局、生产流程和现金流问题,但愿这次难关之后,我们能在很多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未雨绸缪,涅槃重生。当恐惧蔓延到全世界,锁起大门的速度能有多快?
旅行的最后,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叠加,都挡不住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想回家,哪怕家里的疫情比海外严重很多,总好过在外面漂着。同时我也必须承认,在考虑改签回国的航班时,我首先帮父母考虑的是选择外航。看过很多飞机上感染的案例后,我天真地揣测,乘坐外航的同胞比例可能比乘坐国内航空公司的比例稍低一点,或许可以降低与潜伏期病患同乘一个航班的风险,在诸多巨大不确定性中,这是我唯一能试着控制的变量了。但与此同时,我忽略掉了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在极端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可能随时关闭,航班也可以说取消就取消,而且极端情况几乎是毫无征兆地就到来了。印象里反应最快的是英国航空,第一个取消了所有往返中国大陆的航班,汉莎航空紧随其后。父母原定的回国时间是2月1日,眼看着一个个航司取消航班,每半天都有新的政策出台,我的心里也越发焦急。1月30日,有消息称WHO将在瑞士当地时间下午决定是否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列为国际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kelanga.com/mgzz/44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