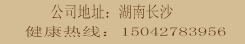壹
老梯田多年塌方出的那一道黄土洼,终于被一簇簇半人高的灌木丛相拥出一个暖暖的缓坡。下大雨的时候,山水不再从半山腰劈头盖脸地往下奔了,规规矩矩地流淌在水渠里,出轨的几率很小,多年来水土走过的痕迹看不见了。四周的小草不再灰眉土脸,郁郁葱葱招惹得秋蝉纠集了蟋蟀、斑蝥、蝗虫、蜻蜓、萤火虫、蝼蛄等,把秋天早早地喊叫到跟前,观赏野菊花是如何从山腰走向河畔——原来是羞羞答答地走去的;倾听坡下那条小河一心一意敲打河床的声音——原来是潺潺湲湲,有时候又是滴滴答答。当然,这也许不是才被人们发现的。才被人们发现的是,缓坡的高处新近多出一个坐北向南的圆形土包,远看特别像一个灰黄色的顿号,仿佛这座山水土流失的事情说完了,后面还有讲不完的故事。前些日子,聋干大就被村子里的人们安放在那个“顿号”里了,但谁也没有想着他以后还会有什么故事。墓碑上的方框里镶着的照片,应该是近几年才照的,头发稀疏柔软了不说,鼻子旁边那个绿豆大的痣也平缓得可以忽略,再也表达不出任何情绪了。与“顿号”平行的不远处,几株脑袋扁平的苹果树,在风和日丽的紧追慢赶下,接二连三地羞涩出了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苹果。几只膘肥体壮的松鼠懒得上树,地上有喜鹊、乌鸦搬运给它们吃也吃不完的新鲜果子,它们才不相信不上树的松鼠就一定不是好松鼠。
柱子在路边挡我车的时候,阳光年少的脸蛋虽然陌生,但神秘的笑仿佛在有远没近地向我提示点什么,我就情愿也不情愿地停了车。上车后,他熟人似的问长问短,我以为我们曾经见过面而被我忽略了,就一一作答。可能是因为他说的事情都在我的记忆中,亲切的感觉顿时塞满了我的车。
“跟您说半天话了,您是不是以为我们是熟人?”柱子问我的语气有点调皮。
“乡里乡亲的,好像不陌生。”
“嘿嘿,其实我们没有见过面,只不过我是蟊司令的孙子,叫柱子。”
“哈哈,你爷爷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大玩伴。他是一个完美的痴人。”
“但我不只是因为我是他的孙子,才厚着脸皮搭您的便车。”
“哦,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您在这一带太有名气了,谁都知道您的名字。您是恢复高考几年后全乡才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您是我爷爷那辈人心目中最励志的人;您是我父辈们最崇拜的人;您是我们这辈人心目中的一个传说。我爷爷说您小时候穿过他的羊皮袄、喝过他的糖精水,所以在我长大的过程中,一直觉得您很亲切,一直想当面叫你一声大叔。想您这几天要路过这里,还真的等上了。”
“嗯,这个好,这个好。我们一起的时候,我沾你爷爷的光多着呢。”
“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不敢拦您的车,现在我长大见世面了。”
“哦哦,你上大学了?”
“嗯,大二了,不上大学不行,我爷爷说的;我爸爸打过我,因为我不向您好好学习。”
“你爷爷就擅长教唆别人。”
“嘿嘿,我能考上大学与您和他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很感激我爷爷,也很感激您。嘿嘿,有意思的是后来考上大学的娃娃,都很感激您。”
“这么说,我和你爷爷是教唆你们‘出轨’的人啦。”
“哈哈,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活在世上难免教唆别人,也难免被人教唆。”
“你爷爷,他还好吗?”
“他去世了。”
“哦……哪一年的事?”
“我高考那年。”
“得了什么病?”
“就年轻时的旧伤,一直没有好。年轻的时候,遇到阴雨天疼痛就复发;年龄大了,扛不住了,癌变了。也怪他当时没有听医生的话,固执地以为父母给的东西摘除不得。”
“哦……天天跟你聋干爷在一起,心里有阴影。”
“嗯,有这方面的原因。他总觉得少了一个器官,人就不完整了。”
“我们一起放牛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娃娃,现在就记得你爷爷吃虫子特别厉害,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蟊司令。”
“呵呵,你们和聋干爷仨人一起放牛的景致是一幅风景画,画中的故事口口相传了许多年,谁都知道。”
“你聋干爷……我小时候叫他聋干大,现在想来他的内心有一个被关闭了的世界,是当时的我看不懂的风景。”
“是的,一个有情有义的世界,一副难以看懂的画。村子里的那个92岁的老五保户殁了后,他也殁了,相差就几天时间。他们一起住了十多年。他一直侍候老五保户睡觉、穿衣吃饭,接送大小便。他的牙齿到老都很好,老五保户临近殁的几年里喝不成奶粉,一喝就拉肚子,全凭他嘴对嘴地喂养饭食。老五保户殁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念念不忘要给他张罗一个婆姨。”
“老五保户老了,说的是你聋干爷年轻时候的事。”
“是啊,从年轻一直说到年老,从来没有忘记。”
“你聋干爷最终都没有娶婆姨?”
“没有嘛。他父母殁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娶婆姨的事,差点都咽不了气。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成天给他张罗婆姨。聋干爷四十二岁那年,倒是娶了一个,也是一个聋哑人,相距很远另一个公社的,叫雅女,人长得漂亮,特别贤惠,但最终还是没过成。”
“女方嫌弃他了?”
“听我爷爷说,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我爷爷说,入洞房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直没有发生。而聋干爷每天后半夜坐在门外的石台子上‘额……嗯……喔……’地叫了好几天。维持了一个多月,一天上午他嘟囔着‘PP……BB……B……’,垂头丧气地打发雅女走了。雅女是哭着走的。走前,她给聋干爷蒸了一袋面的馍,切片晒干后,又装回面袋里。临走那天,她里里外外打扫了卫生,又把聋干爷里里外外所有的衣服洗了一遍。聋干爷牵着驴送了她十里路,然后一路嚎叫回来。驴默默地一路跟着,他都不知道。”
“呃……你给我点根烟。”
“大叔,您的手有点抖。”
“我想知道,然后呢?”
“后来的事就很麻烦了。就因为他没有和女人同过房,埋葬的时候,好些村民不允许他正常地躺在棺材里,强烈要求爬着去另一个世界。棺材都放进墓穴了,但他们挡住,就是不允许埋。他们的理由很充分,谁也没办法反驳,从古至今都是这么个讲究。尽管他们都很同情死者,都说他是一个可怜人,但逝者已去,得为活着的人考虑。”
“小时候听过这个说法,说的是这样的人精血旺盛,做了鬼就是一个不安生的主儿,多数都会返回阳间兴风作浪,而且下手的都是熟悉的人。”
“是的,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所幸的是,后来埋的时候没有让他爬着,因为有人证明他早就不是男人的原始状态了。”
“你爷爷已经过世了,那个能证明的人肯定不是你爷爷。”
“嗯,是我父亲。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曾经多次给人讲聋干爷出轨牲口的笑话,但好多人都一笑了之,说我爷爷记恨聋干爷,编故事羞辱他呢。他临终留下的唯一嘱托,还是文字性的,就说聋干爷三十多岁的时候有过与异性交媾的事情,人们才明白他老人家讲笑话的原因了。尽管这样,那些闹事的村民还是不相信,直到年近九旬老队长极力劝说,才罢休。”
“哈哈……嗝嗝……哈哈……异性?异性……”
“大叔,您眼睛湿润得厉害。”
“他妈的,他妈的……PP……BB……B……”聋干大荡秋千的样子塞满了我的双目,耳朵里尽是“PP……BB……B……额……嗯……喔……”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
贰
聋干大五岁的时候就在我们那一带就很有名气了,有名气不是本该有名气,而是因为他四岁那年过年的三十晚上得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满地打滚,哭喊着说自己是金刚葫芦娃,是孙大圣。家人请来的巫神上蹿下跳了大半天,他妈又用三块厚被子把他捂在炕墙根,他终于安静地睡去了。第二天醒来后,他再也听不见别人说话,也说不成话,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聋哑人了。邻里邻居都窃窃私语,指责他娘,生生地把亲生儿子折磨成一个聋哑人了。他娘后悔得一病不起,不几天就去阴间忏悔去了。方圆百里就他一个又聋又哑的孩子,自然会被许多人想知道,何况他是在去卧牛山庙里调皮捣蛋的时候,吃了供桌上的炸油糕,又对着神神像尿了一泡,得的病。人老几辈子了,谁不知道卧牛山庙里的神神可灵哩。庙虽然破烂不堪,方圆百里的人们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一直相信里面的那个神神求得起、惹不起。那个时候不兴敬神,但不敬可以,谁敢惹呀?哪怕是拿走庙上的一块砖、一片瓦,必然会遭遇不测。多少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不服气的人,都吃了大亏。后来兴敬神了,大人们都告诫自家娃娃不能在庙上胡闹。聋干大从小就调皮,家人给他说了无数次,可他就是不服气,就是不信那个邪,专门奔惹不起的神神而去的。
聋干大姓程,但从小就没有一个程什么的名字,可能是刚好到了起大名的时候,他又聋又哑了,他自己没用,别人也没有用。他家住的村子叫大路峁,所以小时候人们都叫他“大路峁聋娃”,也有人叫他“大路峁哑娃”。因为他是被卧牛山庙里的神神惩罚了的,所以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他很是冷淡,唯恐躲之不及。可能是因为不会听话和不会说话的原因,他从小就只能给生产队放牲口。黄土地上的牲口他都放过,单匹的马、两三匹的骡子、十多头的牛、上百只的羊,从童年到老年,变的是牲口种类和数量,不变的是他与牲口为伍的人生和他脚下永远无法丈量的草场。到了上学年龄,又是因为他听不见老师说话和不会跟着老师念字的原因,没办法上学。尽管没念过书,但他却识得一些字,和人交流还是够用的。小时候只要躲开生产队长,他每天就把牲口群,赶在学校对面的山梁上,偷偷地去跟学生娃娃玩耍。学生娃娃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可能是因为他有不会说话又听不见别人说话、还知道别的娃娃想什么的与众不同。学生上课了,他就趴在教室外面的窗台上听,一边听,一边在石头窗台上用指头蘸着唾沫写,断断续续当了几年的“旁听生”,直到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学生娃娃都觉得他越大越不可爱了,就不跟他耍了。当地人有个说法:个别的牛不长犄角,但这种牛特别劲大,因为本该有的两个犄角却长成两根肋骨了;多了两根肋骨的牛,自然有超牛的地方——皮实、劲大、耐力超好。天下事物本同一理,聋干大眼睛尖、记性好、嗅觉灵敏大概也是这么回事情。
聋干大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才出生,所以他二十岁以前的事情,我都是听大人们说的。他小时候虽然又聋又哑,但特别招大人喜爱,招大人喜爱不仅是因为他不会说话又听不见别人说话,还知道别人想什么的灵动可爱,还因为他逮苍蝇、蚊子的功夫相当了得,只要在窑洞里发现蚊子,他会上前用两个指头直接捉拿;若是遇到苍蝇,他飞起一脚,苍蝇便一命呜呼了。所以,好多成年人成天撵上他,逗乐。他听不懂别人说的其它话,但只要有人喊一声:“苍蝇,蚊子。”他就立马警惕起来,有了便一招毙命,没有他就伸出舌尖,嘟囔几声,然后走掉。长到十二岁的时候,他突然失去了逮苍蝇、蚊子的敏锐。苍蝇蚊子骚扰他,他竟然没有常人敏感,经常被蚊子叮得大包小包的,于是成年人觉得他跑偏了,不再可爱了。没有人找他逗乐了,他就主动黏在别人屁股上,自言自语:“PP……BB……B……”;别人不理他,他就成天抱着一个小狗,在太阳下或月光里的某个角落里痴呆着。
我八岁那年,在家人还在期盼来年光景好一点再让我上学的等待中,第一次和他一起放牛,正式开始面对面地叫他聋干大。由于我年龄太小,大人们就让我跟着相邻生产队的放牛人学习放牛,而聋干大几年前因为放羊出了一个大差错,被他们的队长撤了羊倌的职,无奈地又任了一个牛倌,牛倌比羊倌一天少挣两个工分。我遇到他,就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叫他聋干大。我叫他聋干大,他大约知道,但肯定不是耳朵让他知道的,是从我的说话的口型上判断出来的。根据别人说话的口型,判断出说话的内容,弥补了他逮苍蝇、蚊子超人之处的丢失,但也许这个一技之长跟别人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并没有再让他变得可爱。他那时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婆姨,没有娶婆姨肯定是因为找不到和他“门当户对”的女人。那时候他不再和小狗玩耍了;人们不再叫他“大路峁聋娃”或“大路峁哑娃”了,有的叫他“大路峁聋子”,有的叫“大路峁哑巴”,但叫“大路峁聋子”的人多一些,尽管多一些,多数是背地里说到他时的事情,他看到的越来越少了。无论叫他哪个名字,只要他遇到了,就会表情丰富地笑一下,转身走了。我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鼻子旁边有一个绿豆大、饱满圆润的黑痣,身高在一米六左右,走路有点前倾,皮肤黑得让人看起来有点紧张,头发又粗又硬又密,牙齿是正常的白,但牙龈黑得有点发青,要是平顺的下巴凸出一点,要不是两只眼睛大而传神,我肯定会叫他猩干大。他除了睡觉,手里经常攥着一根两米长的红柳鞭杆,连同上面绑的皮鞭,长度在五米开外。见过几次面后,我才发现他鼻子旁边的黑痣很不一般,高兴了就会藏起来,心情不好了就会流汗,急躁、生气了就会跳动,愤怒了就会发红甚至发紫。
我们一开始交流特别困难。他没有学过哑语,我也没有学过,所以他急躁得有点恨我不是聋哑人,我也急躁得恨他不和我一样会说话。他能发出接近话语的声音很少,除了“PP……B……BB……”,就是两个嘴唇并在一起往出吹气,捎带出的“咪咪……”;有时候动了感情,他会从后脑勺方位启动“额……嗯……喔……”的声音。后一个声音,他主要用来和牲口对话的,声音平白舒缓,那是让牲口知道,他在它们跟前,都乖乖地吃草,别想着庄稼;声音高亢有力、拐弯又突然直冲,那肯定是发现牲口犯错误了,警告呢,若牲口再不立即改正,他肯定会家法伺候,一鞭子下去,哪怕是一头多长了两根肋骨的牛,再皮实,至少身上一缕毛就起飞了;不是针对牛的时候,那声音肯定表达的是极度愤怒,伴随的肯定是黑痣的发红发紫。前一个声音有时候是自言自语,多数情况下是内心情绪的表达,比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假装伸手抓我的裤裆,然后就“咪咪……”地做一个怪异的手势,卷两下舌头,笑得前仰后合。
叁
我们在山上放牛的时候,除了一个我后来一直叫蟊司令干大的人外,他讨厌和成年男人面对面,碰见就躲着走了;若有人硬要和他纠缠,他会摸一摸流汗的痣,脸色凝重地发出一连串的“PP……B……BB……”,成年男人可能懂得他是什么意思,便离开了。他最不讨厌女人,尽管没有女人愿意和他接近或者说话,但他会用翻跟头、拽着树梢荡秋千的办法吸引她们的注意力;如果失败了,他会目送她们走出他的视线,然后摸着跳动的痣,长时间地坐在地上发呆,嘴里不停地念囔:“B……BB……B……BB……”
我们仨人相处的那段时间,我很愉快,经常按照聋干大的编排,玩游戏。蟊干大不是放牲口的,但他一有时间就往山上跑,陪着聋干大放牛,好像有什么别的事。第一次与他们同时见面是在卧牛山上,他们好像搞好要喝酒,但喝了一会儿,聋干大突然暴跳如雷,皮鞭像雨点一样抽打着蟊干大,鼻子旁边的黑痣变成了红颜色。蟊干大不还手,就在地上翻滚躲避,双手死死地抱着酒瓶,一滴酒也没有让洒掉。聋干大打累了,看了看酒瓶,抹了把眼泪,又弯腰把蟊干大拽起,他们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继续喝酒。自从我和聋干大一起放牛后,他就不经常来了。
有我和他一起放牛,聋干大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他经常把我抱在怀里,手伸进我的裤裆里摸。我以前虽然因为可爱,经历过不少干大、干妈的摸,但他摸,我还是很不自在。所以,他摸的时候,我就躲。无奈的是,我一躲,他就吓唬我;“额……嗯……喔……”听起来大人都觉得够瘆人的了,何况我是一个只有八岁的孩子;何况他面前还放着一根能让牛犊皮开肉绽的皮鞭。天气暖和的时候,他总喜欢扒开衣服,在我身上摸虱子,摸到一个,就放进嘴里一个个咬死,活像猴妈妈在心疼猴儿子。我不让他用那种方法捉虱子的话,他就发脾气,就嚎叫。他总喜欢把我搂在怀里,但我越来越不喜欢让他搂我,因为他身上的汗臭混合烟呛味,弄得我呼吸都困难。
他在附近的每个山头上都有自己多年来经营好了的一个人玩耍地方;有的是房子,有的是独木桥,有的是他假想和别人捉迷藏的迷宫……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给我演示一下怎么在那里玩耍。看着他双手高举没完没了地在独木桥上来回穿梭、嬉皮笑脸地在迷宫里穿梭、枕着合拢的双手在树枝编织的房子里睡觉的样子……我仿佛在看一本又一本画在黄土地上的“小人书”,主人翁就他和他的牲口,四周画满了蛇行足迹,还有各式各样山鼠、飞鸟谈情说爱时拉下的粪便,味道却能跃然纸上;暖风、鲜花、阳光、果实,还有人群,尤其是女人,都是画外三心二意的涂抹点缀。要是他能给我讲解“小人书”里的更多故事,我不知道能不能在他面前保证不会泪流满面;要是我能给他重新设计一本“小人书”,就怕一个孩子的想象力不够,无法让他心满意足;要是一个和他同等年岁的人,翻开他的这本“小人书”,不知道能不能合情合理地看懂其中的真实内容。不几天,他就带我把他的“小人书”全部看了一遍。我是一个贪玩的孩子,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早熟,每到一个地方,尽管他给我展示出多么好玩的意思,我都觉得一点快乐感也没有,仿佛是一只野外的猴子为了讨得一点吃的东西,无奈地在给过路人表演、卖萌。
一天,他把我领到一个废旧的窑洞前,用一块红手帕盖住我的头,不许我动,把我吓了个半死,只能乖乖地任他摆布。过了一会,他抱着我进了窑洞,放在炕上,揭开红手帕,在我脸上重重地亲了几口。死烟味呛得我眼泪直流,我以为他要吃了我,吓得浑身哆嗦,他却高兴得手舞足蹈,双手高举,一会是照相姿势,一会又做出吹唢呐的动作……我憨憨地卷缩在铺着杂草土炕的一角,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缓过神来,看了看四周,我才发现窑洞里布置得花花绿绿,甚是好看,想着他可能要在这里安一个家,但安家就得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女人那不就是我的干妈了吗?但我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干妈愿意来这深山野岭居住?不一会儿,他一声不吭地靠在铺盖卷上,不停地搓着一个崭新的手绢;搓着搓着,他哭了,从泪流满面哭到撕心裂肺。但在我看来撕心裂肺和泪流满面差不了多少,因为他没有表达撕心裂肺的足够声音。这又是一本“小人书”,他没有办法给我讲里面的故事,但我隐约感觉到他放牛时间太久,又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想他的妈妈了。我成天早出晚归,也很想妈妈。我们同病相怜,所以我没有保证在他面前不泪流满面。我哭了,他停下哭,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我看了一眼他脸上那发红发紫的痣,颤抖着嘴唇,接连叫了两声聋干大。他肯定没有听见,因为我的嘴堵在他的怀里了。
我先前很怕他,怕他是因为他喜欢摸我的裤裆,他摸的时候用的劲儿特别大,疼得我半天走路都困难。后来他不经常摸我了,但我仍然怕他,因为他用皮鞭抽打树干的时候,树叶纷纷落下、树干瑟瑟发抖;因为他用皮鞭抽打山崖的时候,遍地飞沙走石,河水都在害怕;因为他撒尿的时候,经常对着河畔、山崖、大树“额……嗯……喔……”地叫上好一阵,那声音比冬天黑夜里公猫叫的声音凄惨得多,撒出的尿液味道古怪而难闻。我真想把他的皮鞭偷偷地一把火烧了,特别希望他最好不要喝那么多的水,回到家里再撒尿。好几次,我实在是害怕得不行,回到家里,给大人说,我不想放牛了,原因是聋干大欺负我。但大人们总以为我为了逃避放牛,寻找理由,不予理睬。几天时间里,愁得我看见牛都讨厌,听见他古怪的声音就发抖,闻见他身上的味就想吐,每天眼巴巴地早上盼着太阳迟到,下午再盼着太阳早退。
肆
我的牛群里有一头种牛,叫黑旋风,长得牛高马大,膘肥体壮,四脚若杵、四肢若柱,雄健有力的背部,宽阔平坦,置水不流,两支犄角粗壮尖锐,仿佛两个八字型的擎天柱,不怒自威;走在路上俨然一个行进中的坦克,卧在地上,活像一个停泊在港湾的巡洋舰。打我记得,它从来就没有安生过,打架非常厉害,几乎没有对手;个性充满着攻击性,毁墙坏树是它每天的必修课,驴马骡子被他穿肠破肚者不计其数,秒杀过一只狼、两只狐狸,俨然一个牛世间的“巴图鲁”;具有肉食者趋向,对死尸骨头特别感兴趣,经常咀嚼山中的动物死尸骨头,曾经一口喝干半桶清油;精力充沛,单套犁地不输双牛,强暴母牛,对一切异性跃跃欲试。我最眼红它那平坦的背部,但其它的牛我都骑过,唯独不敢对它有想法;手里的红柳棍对其它任何牛不失威严,唯独落在它身上尽显颤巍,多有忌惮。尽管种种劣迹,无奈其为公牛中之极品,生产队处罚它就投鼠忌器,不能血债血还不说,“革职查办”都不舍得,只好将其锋利犄角尖锯掉,固定了两个木套。多年来它是我们大队下辖四个生产队牛群中唯一的一个久经考验、牛见牛爱,又被广大社员公认了的优良种牛,每年给生产队创造的收入足以顶上一个派出务工的手艺人。它没有固定的犁地伙伴,往往是乏牛、老牛、初上犁沟的小牛与它合作,无论哪种伙伴,都只是出工,没必要出力。
聋干大的牛群里没有种牛,但有一头体格硕大的秦川羯牛,小时候做绝育手术时,遇到一个马大哈兽医,留了一个受了伤的睾丸;成年后温顺不足,雄性时有记忆,喜欢打架斗殴,凭借一对向前直刺的犄角,先天优势特别显著,胜多败少;欺行霸市,经常与大型畜生争夺草场,野狼也惧他三分;更愿意挑逗母牛,遇到发情的母牛,成天不思水草,寸步不离,虽无成事之力,但不放弃力所能及,弄得母牛苦不堪言;黑旋风之外的公牛见了它都唯唯诺诺,气在让贤中,急于无法说理处,称霸所在牛群数载,无牛撼动。它通体黄色,恰好叫黄旋风,仗着其非凡的过去,每每遇到厉害角色,总想一试高下。也许是因为遭遇过相同的命运不济,聋干爷特别喜爱黄旋风,经常给他额外地梳妆打扮,偏吃偏喝,成天拽着它的尾巴出山回家;遇到黄旋风骚情母牛,他会在一旁手舞足蹈地鼓劲,可惜的是黄旋风一次也成功不了,弄得他大半天心情不好,好几次因为母牛没有发情,不配合黄旋风,被他打得皮开肉绽;打架遇到硬茬,若是黄旋风久攻不下,他会替它不讲武德,长鞭出手,让对方瞬间土崩瓦解。黄旋风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牛,有一次河里发洪水,聋干大被挡在了河对岸回不了家,它就冒着生命危险,蹚过齐腰深的水,把聋干大驮了过来。
黑旋风和黄旋风初次见面的时候,发生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打斗,可谓是惊天动地。那是一个太阳不是很尖锐的午后,两个牛群分别在两个斜坡上吃草。我和聋干大坐在两个斜坡交汇的山梁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它们;看牛群是我们两个共同的事,我主要在看聋干大抽烟的同时,观察他的痣,害怕他心情不好。我不知道男人为什么要抽烟,吸进嘴里,又吐出来,无端地制造咳嗽不说,还得时刻忙里偷闲招呼烟具,何苦呢?如果吃饭喝水也这么个闹法,一点意思也没有。他在抽烟的时候,好像一直在思考什么,因为表情一直在变化,笑的时候也开怀,但多数情况下是闷闷不乐,越是闷闷不乐,越抽得报仇似的狠,烟锅嘴都能被他咬烂。他没有办法表达的故事,只能从他的表情和脸上那个黑痣的变化上猜测,但我是一个晚辈,不敢也不会无边无际地猜测他的心思;更是一个孩童,即使无边无际到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怎么可能猜出一个成年人的念想呢?所以,面对他这样一个大人,我连小人书的意思也看不出来。
刚刚从犁沟里卸套的黑旋风和其它耕牛,在旁边的小河里喝了一老阵的水后,就被赶在我的牛群中。一群牛犊和几个待产的母牛正在一个青草茂盛的地方享受肥美,看见黑旋风来了,乖乖地退了出去。黑旋风精神抖擞,阔步踏入半人高的草丛,拉着红柳鞭杆似的阴茎,伸出镰刀似的舌头,左右开弓。其它牛远远地望着,间或啃一口地上的小草,但总是撂不开对黑旋风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kelanga.com/mgly/8045.html